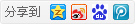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这里,记者就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进行了一些探讨,供读者参考。
“问责风暴”刮起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2003年非典事件中,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被罢官去职。自此,行政问责开始大规模实施,问责走入大众视野中。
2005年底,黑龙江省松花江污染事件暴发,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引咎辞职,成为公务员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位引咎辞职的高层官员。此后,不断有官员因污染事件被问责:2007年江苏省无锡“水危机”引发了一场“环保风暴”,无锡市所辖的宜兴市5位政府官员因在对相关企业违法排污上“工作不到位”或“监管失责”,分别受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行政撤职等处分;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发生“9·8”尾矿库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这是40多年来尾矿库溃坝最严重的一起事故,影响恶劣,孟学农被中央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职务,并同意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为问题被追究责任,“问责风暴”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问责是国家机关对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管理秩序和管理效率,贻误工作,或者损害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所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告诉记者,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过“问责风暴”,人们意识到,政府如果没有履行好相关职责,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损失或者引发了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政府有关官员、政府集体或者职能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表示,“问责风暴”是依法行政原则中职权法定与权责一致的具体体现,行政问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过程中,内在地体现了责任政府的理念,也体现了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的姿态。此外,行政问责制是监督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是否依法行政和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的有效形式。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申请国家赔偿的监督效果相比,行政问责的监督更为直接,因为“问责”直接涉及领导干部的“乌纱帽”和升降奖罚。
“当事故灾难发生、有人被问责之后,所有官员会普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制对公务人员具有很强的警戒作用。”马怀德说。
行政问责艰难前行
认识存误区,行动有偏差
近年来,行政问责的对象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因行政失当失职而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对增强政府责任意识,提高行政应急能力和行政效率具有明显效果。不过,在行政问责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
在我国,目前问责路径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上问下”,即上级对下级问责。“问责被看成了上级对下级具体过失的惩罚。”马怀德说,其实,这只是单向对失误官员的惩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问责,这样容易把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问责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一旦发生问题,包括人大、政府乃至社会公众都可以启动问责程序,而不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上级问责下级”。
现实中,当发生了责任事故之后,人们的惯性思维是“谁是负责人,就找谁”。在一些地方的问责规定中,也都把责任指向了行政首长。“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也就是说,上至行政首长,下至一般行政公务人员,只要有行政失当行为,都应当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马怀德认为,把数量众多的一般公务人员排除在问责对象之外,显然不利于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由党委常委会研究、书记“拍板”,行政首长在党委中往往都担任副手。而按照目前的问责惯例,一旦出现问题只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党委书记却不用担责。“在一个单位,到底是党委书记负责,还是行政首长负责?目前没有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马怀德说,这需要形成规范统一的制度安排。
在以往的一些地方问责中,行政问责名义上是行政首长负责,实际上只追究分管副职领导的责任。行政问责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副职负责制,这就偏离了行政问责的初衷。
“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还限于对比较显性的执行层面的责任追究,问责尚处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过渡阶段。”马怀德说。
问责需要制度化安排
加快立法步伐,严格执法监督
我国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因此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启动问责,制度化安排必不可少。我国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政府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不够,或者过于原则,无法追究。马怀德认为,目前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如此问责才能摆脱“风暴”,走向“常态”。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关于行政问责的立法尝试在不断进行。2003年7月,国内首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出台,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制度的形式先后出台了行政问责制度。2004年7月1日,国内首个省级行政首长问责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2005年2月,《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出台,将“效能革命”制度化。此外,深圳、河北、广西和甘肃等地都出台了行政问责的相关规定。
中央也在行政问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详细列举了9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为问责制度化提供了依据。2009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了七种情形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针对目前行政问责制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我们必须增强法治意识,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制定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各项法律法规,早日实现行政问责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化、制度化。”马怀德表示。
“加快立法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和加强监督”,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说,当前行政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落后于行政处理,行政处理代替司法处罚,外部问责不力等现象,都说明我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执行和监督问题。即使将来立了法,执行和监督问题仍应该是重中之重。